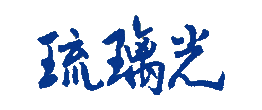| ||
|
【譯註:史丹勒博士最初講華德福教育時,每天第一堂課是講華德福教育的基礎理論—《人學》,第二堂是《教師實作指南》,第三堂課就是《教師討論會》。 《人學》已經翻譯完成出版。此專欄將依照此每天上課順序翻譯每天的《教師實作指南》與《教師討論會》。讀者會比較容易看到當時此華德福教育系列演講課程每天的原貌。】 上期是《教師實作指南》第五講 本期為《教師討論會》第五講 《教師討論會》第五講 講於斯圖加特 1919.08.26 魯道夫•史丹勒 史丹勒博士:最重要的是,伴隨著我們所有的其他工作,我們還應該培養清晰的表達能力。這件事會有一種影響,有一種效用。我這裡有一些我為另一個場合而擬定的句子,它們沒有特別深刻的意義,但其構造是為了使語音器官在各種運動中很自然的被激活。我希望你們把這些句子傳閱並輪流重複,不要覺得尷尬,這樣透過不斷的練習,它們可以使我們的發音器官變得靈活; 可以這麼說,我們可以讓這些器官做槓上體操。史丹勒夫人會先說出這些句子,因為這應該是有藝術性的說出,我會請你們每個人跟著她重複這些句子。寫出這些句子不是為了有意思或有意義,而是為了要讓語音器官「做體操」。(以下是德文,讀者可用Google翻譯內附的誦唸功能學習誦念,活動語音器官,對非德文的語言應該也需要設計不同的句子來練習) Dass er dir log uns darf es nicht loben 這不是用一般交談的方式發音出來,你要按照音節一個字一個字的念 Nimm nicht Nonnen in nimmermüde Mühlen 此處n雖不斷重複,但是是不同的字母組合,因此語音器官可以進行正確的做體操練習。還有兩個n 聚集在一起的時候,m在這一句「in nimm」之中要發音更長時間,(同時注意)長音的i,短音的i。 Rate mir mehrere Rätsel nur richtig 這一句會讓語音器官進入真正的活躍體操。 我建議你特別注意,找到「聲音」和「音節」的形式本質,要看到你真正長成進入這些形式,於是你便能有意識地說出每個聲音,將「每個」聲音都提升到意識中。言語的一個常見弱點是人們都滑過聲音,同時卻又要了解那言語。最好先透過強調根本不應該強調的音節來把一點搞笑元素帶入你的演講中。例如,演員會故意練習說「friend’ly」(重音在後)而不是「’friendly」(重音在前)! 你必須有意識地發音每個字母。甚至做一些像狄摩西尼 (Demosthenes,古希臘著名的演說家)那樣的事情,也許不用經常做,對你來說也是有好處的。你知道,當他練習演說沒有任何進展時,他就在舌頭上放小石子,透過練習,把聲音增強到可以在湍急的河流旁都聽到他的聲音的程度。他這樣做是為了讓雅典人能夠聽到他的演講。 我現在會請B小姐介紹「氣質」的問題。既然我們在教學中主要是必須考慮到每個個別的孩子,那麼我們就應該最小心地研究其氣質的基礎。當然,當我們上課時,很自然的不可能單獨對待每個孩子。但是,你可以透過將水慢型和土憂型放在一側,將風樂型和火旺型的孩子放在另一側,來給予更多的個人化對待。你可以讓他們參與一種生動的交流,先轉向具有一種氣質的小組講課,然後轉向另一組要他們給出答案,對一組說這個,對另一組說那個。透過這種方式,個人化的對待就會在課堂內自然發生。 問:有人全面介紹了各種氣質的性格及其對待方法。 魯道夫•史丹勒:你很好地描述了我們在這個主題上的談話內容。但是,當你斷言土憂氣質決定了虔誠的傾向時,你可能就太過頭了,但只缺了一個字:「經常」。兒童的土憂性格也可能源自於突顯的自我(利己)主義,但絕不具有宗教傾向。對成年人來說,你可以省略「經常」這個小詞,但對於年幼的孩子來說,土憂的元素往往會掩蓋了突顯的利己主義。土憂的孩子往往依賴著大氣的狀況,也就是天氣常常影響著土憂氣質。風樂的孩子也會依賴大氣狀況,但更多的是他們的情緒、他們的靈魂,而土憂的孩子的身體則是更無意識地受到天氣的影響。 如果我從靈性科學的角度詳細探討這個問題,我就得向你展示「孩子氣」的氣質實際上是如何與業力連結起來的,在孩子的氣質中如何真正出現一些可以被描述為經歷的結果的東西。前世在地球上。讓我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某人一生都對自己非常感興趣。他很孤獨,因此被迫對自己感興趣。因為他經常沉浸於自己,環境的力量使他傾向於將他的靈魂與他的身體結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並且在下一個轉世中,他帶來了一種對外部世界狀況很敏銳的身體本性。他變成了一個風樂的人。因此,當某人在前世被迫獨自生活時,這會妨礙他的進步,於是透過在下一世成為風樂者來調整,有能力注意到周圍的一切。我們不能從道德角度而是要從因果的角度來看業力。當孩子有受到適當的教育時,是一個風樂的孩子,能夠觀察外在世界,可能對孩子的一生有很大的好處。氣質在很大程度上與一個人前世的整個生命和靈魂息息相關。 問:史丹勒博士被要求解釋從年輕到成熟的一生中可能發生的氣質變化。 魯道夫‧史丹勒:如果你還記得我曾經在卡塞爾(Cassel)講過的關於《聖約翰福音》(The Gospel of St. John: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Other Gospels)的課程,你就會記得我對那關於孩子與其父母的關係的說法。我指出,「父親原則」在「肉體」和「我」(此處之「我」是指自我意識體,以下皆同)之中發揮著非常強大的作用,而「母親原則」在乙太體和星芒體之中占主導地位。歌德在寫出以下美麗的文字時,預言了這個真理:從我父親那裡,我擁有了我的身材(與「肉體」相關)和嚴肅的生活行為(與「我」相關)。來自我親愛的母親,是我快樂的本性(與乙太體相連)和創造性幻想中的喜悅(與星芒體相連)。 這些話裡蘊藏著非凡的智慧。人類的生命之中乃是一種非凡的混合與攪和。人類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存有。在人類中,「我」和「肉體」之間存在著確切的關係,「乙太體」和「星芒體」之間也有著一種關係。因此,在一生過程中,一種體的主導地位可以轉變為另一種體的主導地位。例如,在「土憂」氣質中,「我」的主導地位轉變為肉體的主導地位,而在「火旺」的人中,它甚至跨越遺傳,從母親元素傳遞到父親元素,因為星芒體的主導地位轉換進入了「我」的主導地位。 在「土憂」氣質中,「我」在孩子期占主導地位,而在成人期是「肉體」占主導地位。 在「風樂」氣質中,「乙太體」在孩子期占主導地位,成人期則是「星芒體」占主導地位。 在「水慢」氣質中,「肉體」在孩子期占主導地位,成人期是「乙太體」占主導地位。 在「火旺」質中,「星芒體」在孩子期占主導地位,而成人期則是「我」占主導地位。 但只有當你嚴格記住你不能以表格形式排列它們時,你才能對這些事情有一個真實的看法,而且你進入靈性領域越高,這種可能性就越小。 問:有人觀察到,在《業關守護神》和《靈魂的覺醒》(The Guardian of the Threshold, and The Souls’ Awakening)這兩個劇本中人物的名字一系列的變化中,看到了類似以上所說各種體的主導地位變換的情形。 魯道夫•史丹勒:確實是根據事實有這樣的一種變化。這些神秘劇(魯道夫•史丹勒的《四個神秘劇:啟蒙之門、靈魂的緩刑、業關守護神和靈魂的覺醒》),必須盡量少把它們理論化。如果是從理論上提出這個問題,我就無所回答,因為這些人物一直就是根據原樣寫出,純粹是客觀的。它們全部取自現實生活中。最近,在另一場合,我說了劇中的菲利克斯•巴爾德(Felix Balde)真的就是一個生活在特魯毛(Trumau)的人,而這老鞋匠菲利克斯的原型是一位叫沙林格(Scharinger)的人,來自明興多夫(Münchendorf)。菲利克斯仍然保留著那裡村莊的傳統。同樣地,你在我的神秘劇中找到的所有這些角色都是真實的個人。 問:談到民族氣質時,是否也可以說一個人具有這個民族或國家的氣質? 還有另一個問題:民族氣質是透過語言表達出來的嗎? 魯道夫•史丹勒:你說的第一項是對的,但你的第二項不太正確。是可以說確實真正有民族氣質。國家確實有自己的氣質,但個人完全可以超越民族氣質。但一個人不一定會有這種傾向。你必須小心,不要將某個人的個人性質與他整個民族的氣質等同起來。例如,將今日的俄羅斯人與俄羅斯民族的氣質等同起來是錯誤的。後者會是「土憂」的,而今日的俄羅斯人則傾向於「風樂」。 民族氣質的品質是透過各種語言來表現的,所以一個人當然可以說,這個民族的語言是像這樣,另一個民族的語言是像那樣。說英語是徹底「水慢」的語言是沒錯的,而希臘語則異常「風樂」。這些事情可以說是真實事實的跡象。德語具有雙面性,具有非常強烈的「土憂」和非常強烈的「風樂」特徵。當德語以其原始形式出現時,尤其是在哲學語言中,你可以看到這一點。讓我提醒你費希特(Fichte)哲學語言或黑格爾的美學(《Aesthetics》)中的一些段落的美妙品質,你會發現德語的基本特徵以異常清晰的方式表達出來。義大利的民俗靈與「氣體」有著特殊的關係,法國人則與「流體」有特殊的關係,英國人和美國人,尤其是英國人,與「固體地球」有特殊的關係,美國人甚至與地下世界—即「地磁」和「地電」有特殊的關係。然後我們有一個與「光」有關的俄羅斯人,即與「從植物反射回來的地球光」有關的人。 德國的民俗靈與「溫暖」相連,你一眼就能看出它具有雙重性─內在與外在,血液的溫暖與大氣的溫暖。即使在這些基本條件的分佈中,你也會再次發現極性特徵。你立刻就能看到這種極性─德國人本性中的這種分裂,在一切事物中都可以找到。 問:孩子應該要知道任何相關這種氣質分類的事嗎? 魯道夫•史丹勒:這是必須「不讓孩子知道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老師是否對應該隱藏的內容有正確而機智的感受。我們在這裡講的所有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為了賦予老師權威。不「謹慎說話」的老師是不可能成功的。學生不應該根據他們的成績就座,你會發現拒絕孩子們請求坐在一起的要求是對教學有利的。 問:不同氣質的孩子的氣質和外語的選擇有連結關係嗎? 魯道夫•史丹勒:理論上這是正確的,但考慮到目前的情況,不建議考慮這情形。永遠不可能只根據孩子的性情而言是正確的來指導教學。我們還必須記住,兒童必須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出路,我們必須為他們提供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一切。例如,如果在不久的將來,似乎有很多德國孩子沒有學習英語的能力,那麼屈服於這個弱點就不好了。正是那些表現出這種弱點的孩子可能是第一個需要懂英語的人。 問:討論了前一天的任務:考慮全班學生在一個孩子的慫恿下做出了非常惡劣的行為。例如,他們向天花板吐口水。有些人對此問題發表了一些看法。 魯道夫‧史丹勒:插斷了一些評論:等待這樣的事情隨著時間消磨,讓孩子們不再自己做,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方法。你應該始終能夠區分某件事是出於惡意還是出於興奮。我想說的一件事是:即使是最好的老師也會在課堂上有調皮學生,但如果全班都參加,通常是老師的錯。如果不是老師的錯,你總會發現一群孩子站在老師那邊,成為老師的支持。只有老師失敗了,全班才會參與不服從。如果有任何破壞,那麼當然應該糾正它,而且必須由孩子們自己去做—不是付出代價,而是自行糾正。你可以用一個星期天,甚至兩三個星期天來修復任何破壞。請記住,幽默也是使事情簡化為荒唐(好笑)的好方法,尤其是小錯誤。 我給你這個問題來思考,以幫助你了解如何解決當一個孩子煽動其他孩子時發生的事情。為了說明問題的癥結所在,我要跟大家講一個真實發生過的故事。在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老師們無法應付的班級裡,一個十到十二歲的男孩在下課期間走到前面說:「女士們,先生們!你們總是做這種事,不覺得羞恥嗎,你們這些沒出息的人?你們就記住了,如果老師不教你們任何東西,你們就會一直完全愚蠢下去。」 這產生了最奇妙的效果。 我們可以從這一事件中學到一些東西:當班級中很大一部分人因為一個或多個孩子的慫恿而做出這樣的事情時,很有可能通過少數人的影響來恢復秩序。如果有幾個孩子是煽動者,那麼也會有其他人(也許是兩三個)表示反對。孩子們之中幾乎總是會有幾位領導者,所以老師應該挑選兩到三個認為合適的人並安排與他們做交談。老師必須明確指出,這種行為使教學變得不可能,他們應該認識到這一點,並讓他們的影響力讓全班都感受到。這些孩子將擁有與煽動者一樣大的影響力,他們可以讓同學搞清楚狀況。在任何類似的情況下,你都必須考慮孩子如何相互影響。 這裡最重要的是你應該喚起他們的感受,使他們遠離頑皮。老師嚴厲的懲罰只會引起恐懼等等。它永遠不會激勵孩子們做得更好。老師必須盡可能保持冷靜,採取客觀的態度。這並不意味著削弱教師自身的權威。老師肯定可以自己來說:「如果沒有老師,你就什麼也學不到,維持繼續愚蠢。」 但老師應該讓其他孩子來糾正這情形,讓他們自己做,讓同學感到羞恥。 因此,我們訴諸「感受」而不是「審判」。但當全班同學一再的反對老師時,就得往老師身上找錯了。大多數淘氣的產生是因為孩子感到無聊並且與老師缺乏關係。當錯誤不太嚴重時,老師做學生正在做的事情當然是很好的—例如,當學生抱怨時說:「好吧,我當然也可以抱怨!」這樣一來,這個問題就可以說是順勢療法了。順勢療法對於道德教育非常有效。這也是讓孩子們注意力轉到其他方面的好方法(儘管我永遠不會去吸引他們的野心爆發)。然而,一般來說,我們很少需要抱怨這類輕罪。每當你允許班上其他孩子糾正這種惡作劇時,你就是在對「感受」下功夫,以重建被削弱的「權威」。當另一個學生強調必須對老師心存感激時,對權威的尊重就會再次恢復。選擇合適的孩子很重要,你必須了解你的班級,並選擇適合此任務的學生。 如果我教一門課,我可能大膽的嘗試這樣做。我會盡力找到頭目,迫使他盡可能地譴責這種行為,盡可能多說一些壞話,而我會忽略「就是這個學生幹的」這個事實。然後我很快就會結束這件事,以便在孩子們的心中留下一種不確定的感覺,你會發現從這種不確定因素中可以獲得很多東西。而讓其中一名小壞蛋正確又客觀地描述事件,無論如何都不會導致虛偽。我認為任何實際的懲罰都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重要的是要喚起孩子們認識到已經造成的客觀損害和糾正它的必要性。如果在處理這件事上浪費了教學時間,那麼必須在課後時間補好,這不是為了懲罰,而只是為了彌補損失的時間。 我現在要提出一個更心理性質的問題:如果班上有一些相當不健康的「好好孩子」—那些試圖以各種方式討好,有著不斷向老師問這個、問那個、問其他一堆的…這種習慣的孩子,你會如何對待他們?當然你可以把事情看得極為簡單。你可以說:「我根本不會去理會他們」。但這種特殊狀況就會轉變成從其他管道發出:這種好好孩子就漸漸變成對課堂上有害的元素。 (第五講完)
|
 本期目錄 本期目錄 |  上篇文章 上篇文章 |  下篇文章 下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