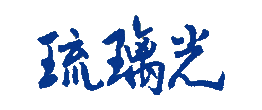| ||
|
【譯註:史丹勒博士最初講華德福教育時,每天的課程安排如下: 第一堂課是講華德福教育的基礎理論—《人學》,第二堂是《教師實作指南》,第三堂是《教師討論會》。 《人學》已經翻譯完成出版。此專欄將依照此每天上課順序翻譯每天的《教師實作指南》與《教師討論會》。讀者會比較容易看到當時此華德福教育系列演講課程每天的原貌。】 上一期是《《教師實作指南》第七講(上),本期為《教師實作指南》第七講(下)。 前期提要 {在九歲之前,不要講自然歷史,因為孩子還活在靈界的印象中,九歲之後講自然歷史,教師心理也要明白,人類是大自然的綜合體,不是獨立於大自然的存在,還有頭部、軀幹、四肢,各有不同的靈性意義,頭部是五官的綜合體,軀幹是來自頭部的一部分,所以五官的輸入都會流向軀幹,四肢則如同來自宇宙,插入人體,腿主要是帶著人站立與行走為人類服務,手和手臂不是為身體工作而是為世界工作。然後講到如何藝術性的介紹人類,眼睛是為了光而存在所以會自動去找光,舌頭是為了味道而存在所以會去找味道成為飲食的器官,用沒有四肢的烏賊與有四肢和尾巴的老鼠來說明四肢的意義。不是直接說明而是用舉動物為例的無意識的方法,透過孩子的「感受」喚醒他們對烏賊和老鼠結構的清晰但基本的認識。認識到高等動物主要是「軀幹」,並且巧妙地在大自然中形成了它們的器官,這些器官主要服務於「軀幹」的需要。對人類來說,情況則是人類的「軀幹」不如高等動物那麼完美。}
然後我們必須喚起孩子們感覺到人類外在形態中最完美的部分—人的四肢是最完美的。如果你沿著高等動物的順序往上直到猿類,你會發現前肢與後肢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所有四個的主要功能都是承載軀幹,並隨之移動,等等。這種將四肢奇妙地分化為腳和手、腿和手臂的現象只發生在人類身上。它表現在直立行走和垂直姿勢的人類素質。就四肢的完整組織而言,沒有任何動物物種的結構像人類一樣完美。 這裡你應該對人類的手臂和手進行非常生動的描述。它們不參與帶著人體活動。手不會為了身體有關的任何事情而接觸大地,而且它們已經被改造成為能夠抓握物體並從事工作。然後你再講到道德方面的內容,這與意志有關。透過孩子們的感受喚醒他們,不是用理論上,而是用強烈的畫面。「例如,你可以用手拿起一支粉筆來寫字;你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只是因為你的手已經被改造,可以用它來工作,而不是承載身體。動物不可能說它的手臂很懶惰,因為它實際上並沒有人類這種手臂。當我們將猿稱為四手生物時,這是一種不準確的說法,因為猿實際上是有四隻像似手臂般的「腿和腳」,而不是四隻手。儘管這些生物的結構是為了攀爬,但實際上這功能只是為身體服務;它們的腳形狀像手,以便在攀爬時可以支撐身體。人類的手和手臂對人體來說已變得毫無用處,而這卻是人類自由的最美麗的外在象徵。沒有比這些手臂和雙手更美妙的人類自由象徵了。人類可以用自己的雙手改造環境,因為人類自己吃飯、滋養自己,他們也可以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為自己做事。 透過描述烏賊、老鼠、羔羊或馬、以及人類,我們逐漸點燃孩子們內心強烈的感覺,低等動物的特質是頭狀的,高等動物的特質是軀幹的,而人類的特質是像四肢的。如果人們不斷地被教導說,人類是因為頭部的功德而成為地球上最完美的生物,這只會向人們灌輸了自負感。這種觀念使人們不知不覺地接受了這樣一種觀念:人類是透過懶惰、昏昏欲睡而變得完美的。他們本能地知道,頭是一塊擱在肩膀上的懶骨頭,不想在世界上移動,而是讓自己被四肢承載。說人類是完美的人是因為頭部、頭部中的懶骨頭而完美,這不是真相;事實上,人類因為四肢,因為參與了世界與其運作而完美。你說一個人不是因為頭部懶骨頭的功德而完美,而是因為四肢活躍而完美,這樣就能使一個人的內心更加有道德。那些只有頭部、必須自己活動的生物,如低等動物,以及那些只能用四肢為軀幹服務的生物,如高等動物,與人類相比,都不夠完美。他們使用四肢的自由度都低於人類。它們的四肢只有一個特定的目的,就是為軀幹服務。然而,對人類來說,雙手,就是完全的處於人類自由的範圍內。 只有當你喚醒人們那種「完美乃是因為他們的四肢而不是因為他們的頭部」這樣的概念時,你才能向人類灌輸一種對這世界的健康感受。透過比較人類與烏賊、老鼠、綿羊或馬的各種描述,你就可以很好地做到這一點。同時你也會認識到,當你描述自然界中任何的活動時,永遠不該排除人類,因為所有大自然的活動,都結合在人類身上。當我們描述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時,我們應該始終將人類置於背景之中。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九歲以後對孩子進行自然科學教育時,必須以人為出發點的原因。 如果你觀察早年的人類,你會發現人類在十歲或十一歲左右會發生一些事情。它並不像發生在幼兒期的這個過程的第一步那麼明顯。當孩子們開始更有意識地移動四肢時,當他們開始搖擺走路時,當他們開始有目的地使用手臂和手時,這就是他們第一次意識到「我」的時候。記憶會回溯到這個時間點,但是不會再超過這一時間點了。當你聽到孩子開始說「我」時,你會明顯的意識到孩子的自我覺知的開始(儘管可能會晚一點發生,會有個別孩子的差異,因為有意識的言語必須首先發展) 。孩子的自我意識的變化在九歲時變得更加強烈,你發現他們更能理解你所說的人與世界的差異。在九歲之前,孩子們與環境的融合比後來要徹底得多。也就是說後來才會開始將自己與周圍環境區分開來。然後你會發現你可以開始和孩子談論一些關於靈魂的事情,而他們不會像他們早些時候聽得那樣缺乏理解。總之,孩子到了這個年齡段,自我覺知會成長更深入、更強。 如果你了解了這些事情,你會發現,在這個年齡段,孩子們會開始用更內心的方式來用字遣詞,變得更加意識到從內心發出的詞語。現在人們對外在現象的關注遠多於對內在現象的關注,因此對九歲、十歲發生的變化關注得太少了。但老師們一定要注重這一點。因此,如果老師們推遲自然歷史的教學(而且應該一直要將人類與其他自然界進行比較)直到這九歲、十歲轉變之後,他們將能夠對一群相當不同的基本心態的孩子們講課。當孩子與大自然的融合程度還比較高時,我們只能以敘述的形式跟他們談論大自然科學的話題。九歲後,我們可以呈現烏賊、老鼠、小羊或馬、以及人類,然後我們就允許談論動物外形與人類外形的關係。 在他們生命中的這個階段之前,如果你把烏賊和頭部關聯起來講,將老鼠與軀幹關聯起來講,同時又在人類的四肢中找到令他們高於其他自然界動物的元素,孩子們將無法了解你說的東西。你真的要利用孩子們在某些特殊年齡所提供的機會,因為如果你按照我所描述的方式應用於自然科學課程,你就會在他們的靈魂中植入非常堅定不移的道德觀念。你不能透過迎合孩子的「智力」來向他們灌輸道德觀念,你必須是迎合他們的「感受和意志」。如果你引導孩子的思想和感受,讓他們明白,只有當他們用手在世界上工作時,他們自己才算是一個完整的人,你就會調動他們的感受和意志。你也必須向他們展示,透過這項活動,人類是如何成為最完美的生物的。你必須描述人的頭部和烏賊之間的關係,人的軀幹和老鼠、小羊或馬之間的關係。透過以這種方式將自己置於事物的大自然秩序中,孩子們吸收了「感受」—是後來會幫助他們了解自己身為人類的「感受」。 如果你試著以一種不讓他們知道你想教他們道德課的方式來塑造自然歷史課程,你就可以將這個特別重要的道德元素植入孩子的靈魂中。但如果你把自然歷史當作與人類分離無關的東西來教授,你就無法向他們灌輸哪怕一絲絲道德的東西。如果你孤立地描述烏賊、老鼠、綿羊或馬,甚至人類,那就只會是一組定義而已。你只能透過從自然界中所有其他生物和功能來建構人類的形象,從而描述人類的特徵。席勒(Schiller)欽佩歌德的自然觀,引導他以一種天真的方式從自然的各個不同面向建構人類。他在一七九○年代初寫給歌德的一封優美的信中表達了這種欽佩。我一再提到這封信,因為它包含了一個應該被吸收到我們的文化中的思想—人類綜合著所有自然的意識。歌德一再說過,人類站在自然的頂峰,感覺自己就是整個大自然世界。他還說,人類身邊的這整個世界也在人類身上得到了一種自我的覺知。 如果你讀過我寫的東西,你會發現我一遍又一遍地引用歌德的話。我引用它們並不是因為我覺得它們令人愉快,而是因為這些想法必須被吸收到我們時代的意識中。這就是為什麼我如此悲傷,最重要的教育著作之一實際上仍然不為人知,或者至少在教育領域沒有取得成果。席勒從歌德天真的自我教育中學到了良好的教育原則,並將這些教育原則傾注到他的《人的美學教育》(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2)一書中。如果我們可以思維超越這些文字並擴展這些理念得到該有的邏輯結論,那麼許多對教育有成效的內容都包含在這些文字中了。席勒透過歌德的見地得出了他的觀點。只要回想一下歌德,作為「大自然為根的人類文明」的代表人物,他從童年起就反對把環境分離的教育原則。他永遠無法允許自己將人類與環境分開。他總是把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放在一起看待,他覺得作為一個人,他與大自然是一體的。這就是為什麼在鋼琴課的教學方式與人的關係脫節時,他是不喜歡鋼琴課的。但當他看到不同手指的功能時,他才開始對這些課程感興趣。當教他「這是拇指名叫湯米,這是食指名叫彼得」時,他就有興趣了,並展示了「湯米‧拇指」和「彼得‧食指」如何彈鋼琴。他始終希望整個人類融入整個大自然之中。 你會記得我提到的其他事情。歌德七歲時,自己建造了一座大自然祭壇。他拿起父親的樂譜架,在上面放上父親植物標本室裡的植物和礦物,並在上面放上一支小香燭,用放大鏡聚焦早晨太陽的光束點燃香燭。這是對偉大自然之神的獻祭—對教育強加給他的一切的反抗。從本質上而言,歌德始終是一個渴望以當今人們應該接受的方式接受教育的人。正是因為歌德在接受了自我教育之後成為了這樣的人,所以他對席勒如此有吸引力,席勒隨後才在他的美學信件中寫下了關於教育的內容。 我的老朋友兼老師施勒爾(Karl Julius Schröer,一八二五~一九○○年,文學史學家,是史丹勒博士在維也納就讀的學校的教授)曾經告訴我,當他還是一名教師時,他必須參加學校委員會來測試未來的教師。但他沒時間準備測試題目。於是,他向未來的教師們詢問了有關席勒美學信件的問題。這些教師們知道各種各樣的事情—包括柏拉圖等等—但是當施勒爾開始向他們詢問席勒的美學信件時,他們反抗了。很快地整個維也納都知道施勒爾在教師考試中提出了有關席勒美學信件的問題。沒有人能理解這些信的意思,沒有人能搞懂這樣的事情。 如果我們在找真正健康的教育思想,甚至可說是最初級的思想,我們就不能不回顧席勒的美學書信等例子,還有 讓‧保羅(Jean Paul德國作家,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先驅。研究教育哲學、愛國主義和政治)的教育學說《萊瓦納》(Levana)。這本書,包含了大量的實踐教學的建議。最近,情況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並不能說席勒的美學信件和 讓‧保羅的教義所帶來的那種衝動已經完全融入了現代教學實踐。 我試著讓你了解如何能「看得出來」孩子生命中的某個時期,大約九歲時,此時在教育方面最好該做什麼。明天我們將討論什麼是最適合十四歲和十五歲的孩子們,以及如何教導他們。透過這種方式,我們將了解從七歲到十五歲的整個時期的結構以及我們作為教師和教育者應該做什麼。課程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而制訂的。今日,人們常常把這個問題抽象化:我們要怎麼培養孩子的能力?但我們必須非常清楚,在「必須發展這些能力」這樣的抽象陳述有任何具體意義之前,你必須先了解什麼是「成長中的個人能力」。 (《教師實作指南》第七講完)
|
 本期目錄 本期目錄 |  上篇文章 上篇文章 |  下篇文章 下篇文章 |